黄河与长江是华夏的枢纽,两条大河之间,还有作为中国地理重要分界线的淮河。淮河流域,人杰地灵,37000cm威尼斯历史学者马俊亚在他的代表作《被牺牲的“局部”: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》中曾概括道:中国历史上的皇权,掌握在三个群体手中,北方少数民族、胡汉混合的关陇集团以及淮北精英。由淮北起家而逐鹿中原者,包括项羽、刘邦、曹操、刘裕、萧衍、朱元璋等。然而,除了帝王将相的事迹,淮北的区域研究,更能让我们探究到社会历史的诸多关键问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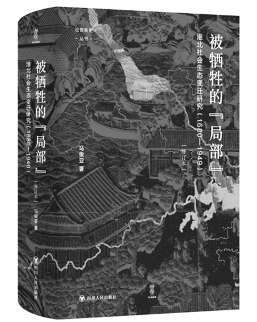

历史上的淮河水灾
“治水”的悲剧
马俊亚对于淮北地区的定义,若以清中期行政区划看,包括江苏的淮安府、徐州府、海州直隶州,安徽的凤阳府、颍州府、泗州直隶州,山东的曹州府、兖州府、济宁直隶州和河南部分区域。以今天区域而言,大体是安徽西部、苏州中北部、山东南部,虽然这一区域隶属于多省,但于地理位置而言,均处于淮河下游地区。
在人们的印象中,“治水”是一件好事,可偏偏对于淮河的治理,直接使淮北地区由盛转衰。明、清两代,南北大运河的畅通至关重要,为了维持航道畅通,治河官吏逼迫黄河之水流向徐、邳地区,相当于人工干预,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水患全部转移到淮北,于是黄河“夺淮入海”。水利专家武同举曾说:“会通既辟,运道完成。河之夺淮自此始。于是运与淮有两不并立之势。”在保障运河的大背景下,黄淮的泛滥也便成为必要的“牺牲”。
我们不禁要问:为什么运河航道必须保障?
据估算,清代每年运送粮食400万石,漕运运费约为1826万两白银,再加上维持运河河道的近千万两白银,整个运河体系的支出,甚至能达到国库收入的50%。然而,通过运河辛苦输送的粮食,因为运输时间久,到达时已变成陈米。很多有权获得漕米的贵族、官员、八旗子弟,便以低价出售,最终导致漕米价格几乎与北方小米价格相当。
然而,如果同样以400万石粮食计算,走海运的全部支出,仅相当于漕运的1/5。其实在元代,来往于南北的海运航线,业已畅通,无论海船制造,还是驾驶技术,明、清时都已具备海运的条件。从史料看,明初辽东停废海运,主要就是由于民间海运到北方的粮食成本太低,以致粮价低落。甚至在道光年间,还曾进行过海运实验,当时同样一批粮食,至少可节约150万两白银。
河务“糊涂账”
不难发现,牺牲淮北、保障漕运的政策,绝非经济指向,而是皇权社会典型的政治“糊涂账”。酿成这种惨剧的原因有二:一是皇帝权威及决策的不容置喙,二是既得利益者的肆意渔利。
明朝统治者,异常在乎位于安徽凤阳的祖陵,因而不惜一切代价,将下游水患的风险,转移至淮北地区。明代潘季驯作为治水能臣,主持修筑高家堰,以解决黄河淤积问题,最终导致在地势极为平坦的淮河腹地,形成一个庞大的人工湖泊,即今天的洪泽湖。本无落差的地势,汇聚如此多的水量,自然容易造成洪涝灾害。马俊亚认为此举“实为淮北生态衰变史上的分水岭”。
迨至清朝,明朝祖陵安危自然不再考虑,然而维持航道、保障漕运,又成为新的“原则”。康熙帝对运河事务甚为关切,经常谈及自己的治河方案,虽强调“一时意见,亦不保其必然”,可是,皇帝的意见哪里有人敢反驳更改?一代代河臣莫非不知道因地制宜的道理?可在皇权社会中,皇帝之命不可能出错,哪怕是错,也要执行下去,正如后世所言:“(康熙帝的指示)后之防河者,奉为一定之制,守而弗失,即千万年可长治也。”如此下来,治河的实际效果自然是“刻舟求剑”。
除了无效治理,明、清两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,“保漕治水”都只是当地政府官员大捞特捞的生财之道。
魏源就曾指出,漕运受惠者绝非百姓或国家,而是海关税侩、通州仓胥、屯丁水手。从基层看,由于漕船在运河中航行有优先权,漕丁会故意阻截运道,敲诈商旅。如天妃闸的闸夫,凡是船只经过,必定勒索,每石粮食索要8厘至1分白银,如果不交,则是通过船闸摆布船只,导致“磕撞立时粉碎”。
从官场看,征漕时,有漕运的八省地方官吏,均加收浮耗,得以利益均沾。剥浅费、过闸费、过淮费、屯官费、仓胥费……各种费用巧立名目。换言之,本来是调配资源的河务,反而成为贪渎腐败的渠道,甚而在淮北地区,河务要员的位置,需金钱贿赂谋求,“河务”成为了贪赃枉法、大肆中饱的“肥肉”。史载当时河员衣食住行,仅有广东洋商、两淮盐商可与之相匹。
一叶知秋,见微知著。淮北治水的悲剧,不单单是个案,它指向的是结构性问题。
盐政的盘剥
淮河入海,水网密布,适合发展盐业。不过,皇权时代的制盐贩盐,绝不只是日常生活的调料贸易,而是朝廷掌握税收的渠道。自古以来,贩私盐者皆属重罪,其破坏的不是市场价格,而是官府的贸易垄断性。
以明朝为例,中央财政每年收入400万两,“其半则取给于盐”。其中,两淮共征课银95万余两,占明朝财政收入的24%。直到上世纪30年代,淮盐税收高达5150万元,折合白银3680万两,占当时全国财政收入的9.3%,同时,3000余万的收入,大致与清中期全国各省实收税款持平。显然,淮北盐业创造的财富颇巨,但这并没有改变百姓艰难的生存状况。
真正制盐的“煎丁”,更像是国家的“奴隶”,他们没有迁徙、改变职业的自由,也没有生产、出售自己产品的权力。《盐城县志》曾描述他们极为悲惨的生存状态:“煎盐灶丁饮咸水而食脱粟,老幼男妇终岁胼胝,出入于尘土煤炱之中。鹑衣百结,面黑如墨,地居中土之极东。当穷冬沍寒,朔风暴作,一无障蔽,其寒彻骨。迨三伏炎烝,正淋漓旺产之时,矮檐灶屋中,烧灼熏蒸如惔如焚。”荒唐的是,他们所生产的盐,能够卖出高昂的价格,而煎丁却连吃饱穿暖都是奢望。不怪乎马俊亚说:“盐税等同于赤裸裸的谋财害命。”
归根到底,盐业是一种政治控制手段,而不是纯粹的经济活动。马俊亚精辟地概括道:“明清盐政就是国家把民众生活必需品加以控制,使之产生垄断暴利,作为皇恩君宠赏赐给利益集团。因此,盐业既是国家财政的支柱,又是把握官场政治的工具。”
马克思曾引用邓宁的说法:“为了100%的利润,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;有300%的利润,它就敢犯任何罪行,甚至冒绞首的危险。”国家垄断的盐业,自然也遵循这一规律。
淮北私盐盛行,比如江船装盐,每捆夹带私盐,称之为“买砠(jū)”;装盐时,将一船盐分为三四船,若有一船失事,即捏报全部损失,将未失事的盐船同样申请补盐,照例免税,到岸之后提前先卖,称之为“淹销补运”;盐船排队等候时,先将盐转卖给私贩,再买私盐补填,称之为“过笼蒸糕”;甚至盐已卖尽,将船故意凿沉消灭贩卖私盐的证据,申报淹销,称之为“放生”。
最终,这种非法生意成为主流,官员在其中参与渔利,形成一个私盐网络。素来严格的雍正帝,面对猖獗的漕运走私,恐其激起事端、妨碍漕运,也曾对走私者无奈地作出让步。清中后期,淮北缉私官员,更是不予查缉,事先达成协议或默契,收取“好处”。如若上级催促,则与走私犯商议,以喽啰顶罪。从盐政中,我们可以发现,官府垄断,给普通劳动者强加重税,毫无益于其生活;高额利润反而引起官、私勾结,衍生出贪污腐败的恶劣生态。
“穷山恶水”?
唐代之前,民谚说“江淮熟,天下足”,宋代之后,逐渐变为“苏湖熟,天下足”,再到明清,淮北区域却成为“穷山恶水”的代名词。究其原因,正是洪涝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。
在公元500到800年的300年里,淮北平原仅发生过5次饥馑;而在1401到1700年(明前期至清前期)的300年里,这里共发生饥馑74次。这种差异绝非气候造成,自然是“人祸”大于天灾。据马俊亚推算,淮河造成的灾害,每年约损失1000万人的口粮。
明、清政府长期于淮北泄洪,当地官府泄放洪水,主要保全强势群体的田地,否则河务官员一定会被弹劾反对。官府只会牺牲平民的土地,保障大地主的利益,他们“视成子河滩民之财产、性命于鸿毛绝不计。”明代人说:“民患虽亟,而运道无虞。”清代人则说:“但知治漕,不顾淹民”。充分体现了淮北普通百姓的处境。
在此情况下,农民根本不可能精耕细作,如果投入大量的资源,一旦田亩被泄洪,则颗粒无收,投入产出不成正比,反而背上更多债务。淮北土地并不贫瘠,面对粮食危机,农民也不会选择耕种荒田,因为一旦开垦,“逃户之田粮差俱负,则征输百役,追令代办”。简言之,谁耕种谁吃亏,所有人都只能在饥饿线上徘徊。
由此,导致淮北地区的两个现象:人身依附、土匪横行。正所谓:“荒岁失收,贫无生计,良者往南佣工,黠者流为盗匪。”当时受灾的淮北农民,前往富家地主处务工,多有只管饭、无工资的情况,主要因为百姓在灾年走投无路,只能苟且偷生,除了成为地主的附庸,别无选择。这种人身依附关系,根本谈不上任何权利,仿若地主的农奴。
俗谚说:“穷山恶水出刁民”。在生命都受到威胁的情形下,也就指望不上人的善意。于是,淮北匪患横行。史载淮北盗匪:“在河南者,由颍亳,在山东者,由徐邳。而流劫之盗乘虚突入矣。惯水斗者,操舟;惯陆行者,利梃。而江淮之盗亦乘机窃发矣。”
与此相对,淮北的富商地主,会充当圩寨寨主(圩寨是寨外围土墙砖石、四角建有炮楼的建筑群),组建强大的武装力量,保障自身的安全和财产。那么,土匪抢劫的对象是谁呢?要不就是一贫如洗的百姓,要不就是铤而走险,冲击大户,无论做何选择,都只会加剧淮北“丛林社会”的险恶。
综上,淮北的悲剧,实际上是皇权社会的症结所在——在王朝时代,淮北只有皇帝,没有国家;只有官僚,没有政府。